“秦始皇统一岭南后,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在缚娄人居住地置傅罗县,隶南海郡,县治在梁化屯(今惠东县梁化镇)” (《惠州市志》记载)。表明今惠东梁化是古代主要的“缚娄人居住地”之一,为缚娄人聚居的中心,成为缚娄国建邦之地,笔者对这一论断完全赞同。并经过系列调查考证认为:古代缚娄国实际上是建在梁化,梁化是古代缚娄国的国都、大本营,它和建在梁化的古县、古郡同出一个地方。
一、“梁化”的涵义,是古代“缚娄”的演化和诠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于公元前214年发诸亡人、赘婿、贾人略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秦时五岭以南为陆梁地,意为岭南之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亦指民住山陆而强梁。梁化,即表示“陆梁”已被开化,故名。《惠州府志》有谓“归化山府东南百里,俗呼鸡笼山”,此山取名“归化”,亦有“归服开化”之意。
以上引述,不但表明了“梁化”的名由涵义,而且与梁化的早期发展历史相吻合。从梁化出土的众多文物可以看出,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在梁化一带繁衍生息,从事捕捞、狩猎和原始的农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梁化已是岭南蛮夷族群聚居的一大据点,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蛮荒邦国即缚娄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军南下平越屯兵梁化,直捣“缚娄”老巢,平蛮建政,于梁化屯置南海郡属傅罗县,化“邦”为“县”,强悍的“陆梁”人始被“归化”,收归正统管辖了。
“缚娄”之名也与“梁化”有着密切联系:一是“缚娄”亦作“部娄”解,左丘明《左传》中有“部娄无松柏”之句,意指山包、土丘、小阜,这与属于丘陵山包地带的梁化地理地貌十分吻合,而且“缚娄”与“部娄”音相近,在古代,“因地形而名”也是一种常用的命名习惯。二是“部娄”、 “缚娄”之名,也与后来建在梁化的“傅罗(娄)县”“博罗县”音、义相近,似出一辙。
越族无文字,“缚娄” 与“傅罗”起初为汉语口音相传,但是后来随着县制的建立和南下中原人“与越杂居者”的增多以及文字的逐渐输入,在“以字表音”记录时,“缚娄” 与“傅罗”不但音同,而且义近。“缚”的本义是用绳缠束、捆绑、约束;“娄”的本义是指中空,又指“用绳系”(《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中有“牛马维娄”句,何休注:“系马曰维,系牛曰娄”)。 傅罗的“傅”字,本义是辅助、辅佐,又指一种植物名“结缕草”,状似白茅草,长于山坡荒地,可编织草铺盖房用(梁化多为山坡且长此草,现仍有茅爷山、丝茅田、茅埔等地名);“罗”的本义是用绳子编成的网来捕鸟。以上不难看出,“缚娄”与“傅罗”四字都有“草绳”的共同含义,“缚娄国”与“傅罗县”同出梁化也就不奇怪了。
有的专家认为“缚娄”即“扶娄”,为一声之转,周朝的扶娄、战国的缚娄、是同一个地方,是“傅罗”一名的历史沿袭。
还有一种说法,“缚娄”“傅罗”的“娄”和“罗”各加一“口”组成“喽啰”,“喽啰”的本义为英雄好汉,在古代梁化从“缚娄”到“傅罗”的转化中,无疑是对被开化的“缚娄”人的一种褒许,同时也蕴含了这两个名称在文字表达上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二、梁化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是古代“缚娄”部族安营扎寨的天然屏障
梁化地处广东省和惠州市的东南部, 梁化四面环山,中部为小盆地。北部和东部为崇山峻岭、重峦叠嶂,属莲花山脉的延伸,鸡笼山(归化山)、坪天嶂、石人嶂连成一片,海拔都在800米以上,其中坪天嶂海拔1069米,石人嶂1035米;南部和西部大都为小山矮岭,丘陵起伏。
梁化河,相传过去河宽水深,舟舸通航,发源于坪天嶂、归化山(鸡笼山)西南麓,流经梁化屯、衙门沥自东北向西南贯通全境,到惠阳平潭新墟汇入西枝江,全长41公里,下游宽30—50米。
古代四面环山的梁化,分别有三大险坳要冲扼守着梁化三大出口,一个是扼守往惠州、广州城邑的叫山角坳,一个是扼守往紫金、龙川北部山区的叫蕉船坳,一个是扼守往海丰、揭阳粤东沿海的叫白泥坳。这三个险坳成为当时固守邦、县、郡唯一的陆路出口,至今这三个坳仍然是梁化三大通道出口。其中白泥坳和山角坳,均靠近梁化河,险要坳口与傍山河埠咫尺相依,蕉船坳距离横沥东江渡口仅几公里,成为通往粤东沿海、惠州和广州城邑及河源等地的水陆两路通道的关口。正如李存在《惠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指出:“(古代梁化)既扼守着番禺(今广州)至龙川的河运咽喉,又控制着番禺至揭阳交通的水陆转运点;既是秦朝统治原缚娄国越族居民的行政中心,又是镇守粤东交通枢纽职能的军事中心,是一个典型的古代城市。”
从惠州地理上看,梁化紧邻东江、西枝江两大江河,梁化河流经梁化全境,“两江一河”(东江、西枝江、梁化河)相互贯通,古代水路可直达南海郡、龙川县,可见环境独特,位置重要。从梁化地理上看,四面环山的梁化,两面背靠重峦叠嶂,两面环绕部娄矮岭,三坳三水,水陆相依,山坳崎岖,河流畅达,关隘险要,造就了梁化易出难进、易守难攻、安可乐居、危可退保的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因而也自然成为古代“缚娄”族人聚居和建都的首选地方。
三、梁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是古代“缚娄”部族集聚繁衍的首选之地
早期岭南蛮人多居山洞,俚獠混杂,强悍愚顽,自守一方。梁化除了“坳险”,还有“洞多”。细数之,在现梁化区域内及周边附近,仍保留有十个以“洞”为名的地方,即燕岩洞(梁化)、上洞(梁化)、大和洞(梁化)、小和洞(梁化)、谢洞(梁化)、三百洞(森柏洞,横沥)、沙洞(横沥)、孙洞(酸洞,平潭)、池洞、李洞(白花)。其中位于梁化屯东、北两面连绵大山脚下的是燕岩洞 ,是至今保留较好而又奇特出名的一个大岩洞,它位于坪天嶂山脚下,现梁化省级森林公园(原为市属梁化国营林场)内,向北通往紫金方向。洞口高2米多、宽3米多,进了洞门口里面又有两个洞口,分两层入岩洞,洞内有宽有窄,蜿蜒曲折,最宽处25—30米,面积约100平方米。燕岩洞深邃莫测,洞口门前面原是一大片可耕地,而且傍依梁化河上游,不言而喻,这在古代梁化是蛮人“随洞而居”、繁衍生息的理想地方。
古代梁化四周大小山岭木荣树茂、葱茏叠翠(今北有梁化省级森林公园、梁化梅园,东有花树下水库、省级古田自然保护区),中间盆地广阔,为草肥水美、农兴畜旺的丰腴之地。梁化河蜿蜒流经全境,支流繁多,水网交错。梁化地处低纬度,年平均气温21.7度,年平均降雨量1646毫米,常年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四季常青,资源丰富。 梁化固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在梁化一带捕捞狩猎、原始农耕和繁衍生息奠定了良好的生态基础,也为春秋战国时期吸引、聚集蛮人,壮大族群,建立“缚娄国”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
四、梁化八百年县郡发展,是古代缚娄国的催化和延伸
据市县志书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略定陆梁地后,在梁化置南海郡属傅罗县,县治在梁化屯。“其辖境大致包括今惠州市的惠城、惠阳、惠 东、博罗和龙门的东南部,包括东莞市、深圳市、汕尾市和揭阳市的 惠来县西部、河源市的紫金县大部分地方”(《惠州市志》)。三国吴末甘露元年(公元265年),傅罗县改名博罗县,县治在梁化屯。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 ,南海郡东部划出新置东官郡,同时在博罗县(治所在梁化屯)属地析置欣乐、安怀县,南齐建武四年(公元497年),东官郡徙治梁化(博罗县城、东官郡城同在梁化)。南朝梁天监二年(公元503年),置梁化郡(东官郡改为梁化郡),郡治所在梁化屯。“辖欣乐、博罗、龙川、河源、雷乡等5县。博罗县治从梁化迁至浮碇岗西麓(今罗阳镇东侧葫芦岭)”(《惠州市志》)。隋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欣乐、怀安合并为归善县,县治置于白鹤峰下,为梁化郡归善县,仍属梁化郡辖。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废梁化郡置循州(惠州),设立总管府,成为惠州府治的开始,府、县治所在今惠城区。
其中特别要指出的是,惠州明朝著名三尚书之一的韩日缵编纂的明崇祯本《博罗县志》,明确记录:“最古置县自秦始皇三十三年,与龙川并隶于南海郡,龙川令尉佗保有岭表,而博罗县令姓名不著,岂才不佗若耶!县治梁化,在迤东百余里,后析县地为归善海丰,置梁化郡,徙治浮碇岗西,自梁武帝天监元年,今仍之,数千余年……”。韩系明代著名国史和方志大家,崇祯皇帝曾称赞过他的“实学、史识”。他学富五车、博览史料、精通国史。据载,他以纂修国史的身份纂修了博罗历史上首部成书之县志。他所精心纂修而成的《博罗县志》(明崇祯本),“史笔谨严”“有功于文献”,颇受后人的称赞,亦成为后来许多地方志的范本,之后《博罗县志》的康熙本、乾隆本、光绪本等基本上都是以他纂修的县志作为基础。他对早期梁化古县郡建制的论断和观点,具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性和唯一性。
古代梁化建制发展,亦同岭南乃至其他地方古代城市发展一样,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延续八百年的县郡政制,立之有源,建之有据。南梁时之所以在梁化建郡,是因为梁化已经过几百年的建县历史,换言之,梁化的郡治,是在傅罗、博罗、怀安县制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汉时之所以在梁化建县,是因为梁化自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结邦立国”“自守一方”。对此,秦始皇派军队“南取百越之地”时,必然重兵对付,由此而屯兵梁化,剑指“缚娄”之邦,令之“俯首系颈”,进而“开化”顽夷,同中原一样实行郡县制,在“陆梁”之地的梁化建起岭东地区第一个县:傅罗县。
总而言之,春秋战国时期建在梁化的“缚娄国”,是梁化县、郡建制发展的基础和导因,梁化历经的邦—县—郡,是惠州府、归善县、博罗县乃至周边县区的立府(县)之根、建制之源、人文之祖,是惠州乃至周边地区早期历史发展的有力印证。直到南宋,朱熹在宋淳熙六年所撰《林氏世系总纪》中的 “举闽州凡称林氏皆禄公后叶也。世远支分,播满海内。北自玉融、长乐、以通吴夏。南自晋安以至梁化、潮阳,无不聚斯……”一段记述,仍以“梁化”取代“惠州”。明末清初徙居于梁化柴行街的林氏家族,其祠堂正厅有一副木雕穿凿的对联:“德绍清河远承先绪;庆开旧郡祥启后人”,揭示了林氏发源于“清河”、开基于梁化的族脉,以教诲族裔后人慎终追远,承前启后,联中以“旧郡”指代梁化,含有“以徙居梁化为庆”之义。直到清末,“梁化旧邦”还声名远播。相传当时梁化龙形拳宗师林合带狮队到东莞四大围切磋交流武术时,他以精湛的武艺和高尚的武德令当地拳师和民众折服,东莞四大围人特意将一幅写有“梁化旧邦”的大匾赠给林合狮队,并一路放鞭炮恭送林合狮队回梁化。从这个广泛流传的真实故事中,可见“梁化旧邦”在岭南广大地区早已深入人心,享誉民间。创作于1946年的《梁化中学校歌》,歌词中亦有“故郡声名垂表芳,校名依旧邦”之句,足见其历史影响的深远和一脉相承的印记。
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万历年初,惠州府衙在中山公园前建立的木式大牌楼上(后改为石砌),分两面在横匾上镌刻有“梁化旧邦”“岭东雄郡”八个大字(注:“梁化旧邦”刻在正面,“岭东雄郡”刻在背面)。 “ 旧邦”意指故国、旧国即缚娄国(“旧邦”最早出现在三千年前《诗经.大雅.文王》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雄郡”意指梁化郡。揭示了梁化经历过缚娄国—傅罗县(博罗县)—梁化郡建制发展历史,又反映了古代梁化在粤东的政治、地理和历史文化地位。
历史的长河流经两千多年,到清光绪四年(1878),调任惠州知府的张联桂,上任伊始,便风尘仆仆亲赴梁化之行,并作诗《梁化行》一首。其在诗中小序指出:“此州为梁化故地,作梁化行见志。”诗中荡气回肠的诗句,笔者感慨系之。作为“故地”的知府大人,对“祖地”梁化的尊崇和关注,可见一斑。可谓是:历史可鉴,初心可嘉。
五、广东三大俚僚部落之一的“梁化邓马头”部落扎根梁化,是古代缚娄国的赓续和演化
无独有偶,翻开《隋书· 谯国夫人传》,其中有一段如斯记述:“(夫人)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
对此,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徐祖祥进一步作出阐述,他在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民族教育》(2018.12.25)刊物上发表的《俚人:一个尊崇铜鼓的部族》一文中指出:“据《隋书•谯国夫人传》载,打败王仲宣后,冼夫人护卫裴矩巡抚诸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首领陈坦、冈州(今广东新会北)首领冯岑翁、梁化(今广东惠阳东南)首领邓马头、藤州(今广西藤县)首领李光略、罗州(今广东化州)首领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裴矩承制署诸渠帅(编者注:渠帅指首领或部落酋长)为刺史、县令。”
该传记载的5大“俚僚”部落首领,即苍梧的陈坦,冈州的冯岑翁、梁化的邓马头、藤州的李光略和罗州的庞靖,他们部落的分布,其中2个(苍梧和藤州)现属广西,3个(冈州、梁化和化州)属广东。翻开广东地图,从地理上分析,可看出广东的3个部落化州、新会北、梁化,分别位于粤西、粤中南、粤东3个区域。
从南朝梁时梁化建郡至隋初,梁化的俚僚部落已成为岭南地区(含广东广西)有名的少数民族部落之一,部落首领邓马头亦是岭南的“名帅”之一,这从《隋书》的记载便可得到印证。同时,这也是梁化先秦的“缚娄”部族历经长期演化的结果,同样也印证了集聚于梁化的“缚娄人”到“俚僚人”的嬗变关系。梁化早期的“缚娄人”,为古代越族人,俗称“南蛮子”“夷蛮人”,亦属百越之土著民族。“俚僚”即为其后裔之泛称。梁化之所为成为古代“缚娄人”部落的大本营,主要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而梁化成为全省三大“俚僚人”部落之一的聚集之地,也可以说是古代缚娄国的赓续和演化
六、梁化出土的众多早期文物及现存遗迹遗址,是古代“缚娄”建邦的物化见证
50年代中期,在梁化花树下(梁化屯东南约5公里处)建设水库时,出土了一批早期的珍贵文物。之后又陆续在梁化屯等处发现一些残存的古代遗迹和文物。从1955年始至今,不但连续不断有所系列发现,而且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所属的时代跨度广,从原始的新石器时代到唐宋,几乎每个年代都有。在出土的古代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的石戈、石锛、石镞、石铲等,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鼎、陶碗、陶罐等,还有隋唐时期的“崑山片玉”石磨等等。这些珍贵文物分别收藏于省、市、县博书馆,有的为全国仅有,有的分别成为省、市、县博书馆的“镇馆之宝”。古代梁化屯分别有东、西、南、北城门,其中东门有后花园,由于时代久远,历经沧桑,城楼门、围墙等大都不复保留。下面,选择梁化花树下、梁化屯等处出土的部分古文物和现梁化古遗址作逐一配图简介:

图1:新石器时代石戈,现收藏于省博物馆
1.石戈(图1)。1956年在花树下建水库时在库区出土,为新石器时代的一种石器,现收藏于省博物馆。此外还有石锛、石镞、石铲等,说明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梁化繁衍生息。

图2:春秋战国时期的三足圆形青铜鼎,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
2.青铜鼎(图2)。1956年建造花树下水库时在库区柯木山取土筑坝时出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现收藏于省博物馆,被誉为省博物馆“镇馆之宝”。青铜鼎三足,圆形,口径16.5厘米,高16.6厘米,纹饰上半部为饕餮纹,下半部为蝉纹。三足圆形青铜鼎的出土,留下了梁化春秋战国时期邦国贵族的生活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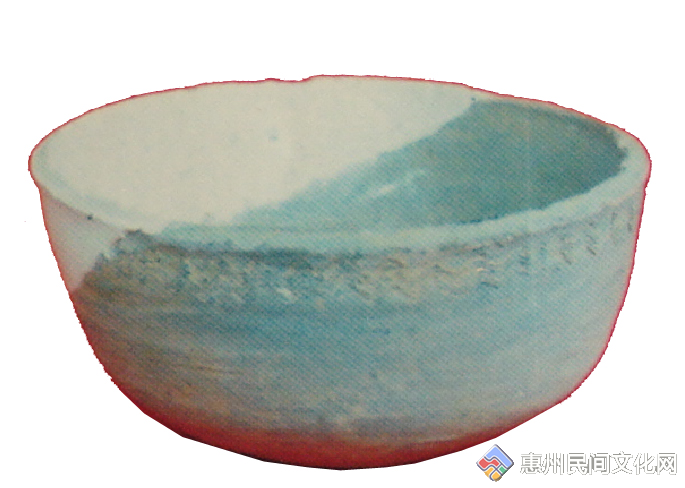
图3:战国时期的陶碗陶罐,现收藏于惠东县博物馆
3.陶罐、陶碗(图3)。1975年在 梁化屯沙公岭出土,为战国时期的陶器,现收藏于县博物馆。陶罐为篦点纹,陶碗为水波纹。陶罐、陶碗的出土也透露了战国时期邦国族民的生活气息。

图4:唐代“崑山片玉”石磨,现收藏于惠州市博物馆,为市博物馆“镇馆之宝”
4.“崑山片玉”石磨(图4)。1954年建造花树下水库时在银屎坑取土筑坝时出土,为唐代器物,与石磨一起出土的还有唐代的碗等器物,现收藏于市博物馆,为市博物馆的“镇馆之物”。石磨为红砂岩质地,浅铁红色,形制与现代石磨相似,最宽为45厘米,通高30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为圆柱形,外壁中饰一圆形方孔钱币状浮雕,上阳刻对读“崑山片玉”四字,下半部有磨心、磨齿和凹槽。石磨制作精细,纹饰流畅,艺术性较高。出土的石磨虽属唐代,其时梁化已撤郡,但隋唐时代梁化旧城生活亦可见一斑。

图5:梁化屯沙公岭战国时期遗址
5.梁化屯沙公岭战国时期古遗址(图5)。梁化屯沙公岭坐落在梁化盆地的南面,梁化河在它的背面自东西流过。沙公岭是直径约200米的小山岗,相对高度约10米。1975年,当地群众在该地垦荒时,发现战国时期的蓖点弦纹陶瓿1个,南北朝时期的青釉瓮1个。 1984年,县文物普查组在该处附近发现有东汉时期的墓砖和春秋至秦汉时期的云雷纹、米字纹、方格纹、水波纹等多种几何纹饰的陶梁化屯沙公岭战国时期的古遗址及其出土的文物,为秦军屯兵梁化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提供了佐证。

图6:梁化花树下战国时期至唐代遗址
6.梁化花树下战国时期至唐代古遗址(图6)。花树下坐落在梁化盆地东面的丘陵地带。1955年春,在花树下水库工地的柯木山、观音山、桐子岭、银屎坑、油麻排等地分别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唐代的遗物。1956年春,省文物工作队曾到该处调查发掘,并在水库主坝西北约100米处,采集到方格纹陶片10件,绳纹陶片2件,米字印纹陶片1件,残石器3件;在银屎坑发现唐代石磨一座;在柯木山发现饕餮纹铜鼎一个,汉代陶罐一个,板岩磨制石杵1件,该石杵器身为椭圆长条形,长14、宽3.4、厚2.7厘米,全器磨光,侧缘呈钝棱,上下端均磨光;陶钵1件,该陶钵通高9.2厘米,口径11厘米,为灰色硬陶,器身满布方格印纹,腹部线纹相同;陶缶1个,该陶缶通高13厘米,口径15.2厘米,为灰色软陶,器身满饰方格纹;陶纺轮1个,为灰色硬陶,扁圆形,中央有穿,火温较高,表面留有轮旋痕。花树下出土的文物,数量多,时代跨度大,凸显了梁化古国、古县郡核心区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文化传承的久远。
此后,梁化亦相继陆续出土发现一些古代文物。2014年3月,又在梁化屯发现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小石锛、周朝时期陶器、唐宋古钱和一些明清时期的瓷块等。相信今后还将会不断有更多、更重要的新发现。尤其是花树下水库周边和水下,以及包括沙公岭老圩河城隍庙等处在内的梁化屯全境,尚存在很多未知而待发现的可塑性。
顺便一提的是,至于除梁化之外其他地方发现的一些早期文物,不排除是随着梁化迁县、撤郡“搬家”时从梁化本地带走的可能。同时,五十年代花树下、梁化屯等地出土的文物大多较珍贵的被收入省博物馆,留给市县的不很多,但有的却很珍贵,为全国独有。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梁化从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衍传到缚娄国的建立,再到古县、古郡建制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互为因果的。在立足于大量史实的基础上,只要用联系的观点,辩证地分析梁化隋以前的建制发展,就不难得出结论:梁化在建县置郡之前,就是缚娄国的诞生之地、立国之都。 (重修定于2025.4.16)
![]()

周汉光,广东省惠东县人。曾任惠东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对岭南地方历史、民俗风情、寺庙祠堂、古民居、客家方言、民间文学以及客家美食等做过系列调查研究,相应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其中“宗教民俗”和“四大传统节俗” 系列散文分别获评2015年和2016年度“惠州民间文化优秀成果奖”。著有《实用文书和诗文选编》《古郡风韵说梁化》《风情雅韵》等作品集,其中散文集《古郡风韵说梁化》分获“广东省第八届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三等奖和“2017年惠州市民间文化优秀成果新圆奖”。
